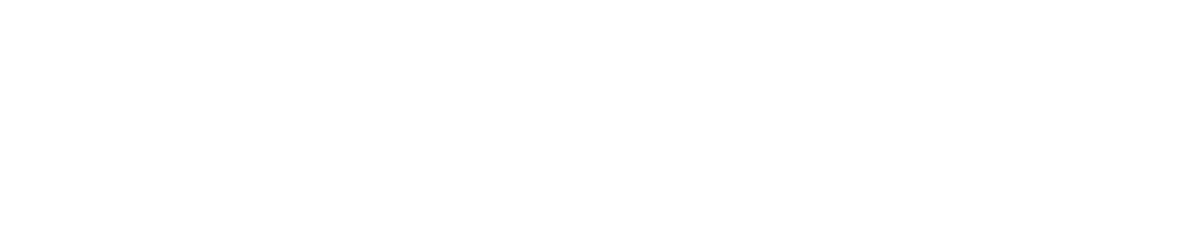從懂事以來就喜歡看書,有時到寺廟拜拜都會找一些因果書,因為是故事性質,淺顯易懂,又有警世的意味,每次看了就會提醒自己不可以作惡,是會有果報的。也自以為是如故事中人一樣是好人,自以為自己不會作壞事,善有善報。對家裡的信仰並不是很清楚,應該算是道教吧!逢年過節媽媽都會帶我們到廟裡去拜拜,末學也喜歡,大概覺得拜拜能保平安吧!依稀記得小的時候身體很差,曾經過給 觀世音菩薩作義子,當時就會有一個紅色的香火,上面印著「觀世音菩薩」五個字,給你掛在脖子上,表示你是 觀世音菩薩的義子,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很高興,也覺得很光榮。家裡也曾經短暫供奉過 觀世音菩薩,媽媽說要早晚供茶、供香,末學也很高興的做。
承領麗娟菩薩的慈悲,讓末學有這樣特殊的因緣來作法布施。末學雖然學歷有所限制,文辭不通順且不達意,但是末學還是很樂意將學佛的因緣及過程來分享,那就是渴求生命實相的真諦,以及道業如何在日常家庭生活與之並進、互相勉勵而邁向正覺的大道。
十八年對一個四十幾歲的人而言,無疑是其最精華與最輝煌的歲月,而我的這段歲月就大部分奉獻在一貫道的道場裡。這些日子裡,個人歷經結婚生子、事業的衝刺等等,在一貫道道場上也歷經「清口茹素」、「捨身辦道」、「開設佛堂」與「開荒下種」(出國開荒辦道)。所以,個人無論是在家庭或者是在一貫道的道場上,可說是皆已完成一個階段性的任務。在這些時日,我曾經期盼自己能終老於一貫道;甚至祈願到老時,還能拄著拐杖到佛堂講課等等。然而如今,這些期盼已不復存在!這些願望也已不能再實現!只因為自己對生命的實相與未來的修行方向已有重新的認識,與其將生命盡付於對佛法不能知亦不能證的未來,倒不如切切實實地待在正法道場,即使是默默而無聞也都有利益。換言之,一個非正法的道場,絕不會是我終其一生安住之所。因終老於正法道場是我所盼,安住於正法道場是我所願。於是,我選擇離開待了多達十八年的一貫道……。
一、在法上的樂
自從深入學佛以來,人生確實變得比以前「無趣」,以跟我同年齡那些正值青春年華的7年級生來說,我現在過的生活真的是有夠無趣的吧!因少了世間人所喜愛的基本娛樂——到處逛街遊玩吃吃喝喝、KTV 唱歌、夜店飲酒狂歡;雖然我也有自己所喜歡的世間娛樂。
我從十來歲便離開父母到外縣市求學,學校畢業也同時獲得一份工作,即離開父母由南部鄉下隻身北上工作,因此成為爾後生活與生存的基礎。但是舉目無親又相當年輕更顯得無助,雖然後來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,角色身分的扮演也變得多重性。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,還要兼顧著家庭、養育、教育小孩,甚至於又是要母兼父職……。以及為了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必須要協助娘家改善生活,並且做了一些安排與照顧,之後各種的境界也逐漸浮現出來,都要一一去面對與解決。雖然無助但也算堅強勇敢,凡事很會忍耐亦很相信因果,所以不喜歡抱怨也不想增加娘家父母的擔心,可是會思考人怎麼會那麼的 苦?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煩惱?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道教廟宇拜拜,像一般世俗人一樣拿香跟著拜,求家人平安……等,但是煩惱依舊未改善。一晃眼,時間過得很快,已經由少女到了中年,歷盡滄桑,一直就想著人生那麼的苦,便起念想學修行,看看是否可以轉變命運?但又苦於周邊無學佛的同事或親朋好友,自己又不知門路。
接觸佛教正覺同修會 蕭平實導師的書後,總認為 平實導師的書極有特色,迥異於坊間諸方大師的議論。平實導師書本所述內容,法義之正確高妙,無人能出其右,而有著最根本重要性的,當推 平實導師所樹立的「第八識真心如來藏為法界唯一本源」之論點,我即是因為 平實導師的這個立論才知佛法真有中心,才知佛法是有所趣向的。以如來藏為中心的正確觀點,較之當代其他謬說,真的是顯出以簡馭繁、綱舉目張的效果。並且 平實導師書中的佛法有整體架構,不僅來路去路清楚,當下一步也是清清楚楚。平實導師之所以為導師,正是能夠在現代一片迷惘的佛教界中,為學人釐清整個佛法內容,鋪陳前後修學次第,導學人向於正途,指出真正佛法大城之所向,這點絕對是目前佛教界所沒有的。受 平實導師的這種啟蒙,我於佛法認知中有了正確的目標與方法,一改過去懵懂無知的錯誤觀念,並由於 平實導師所樹立的真正法義,讓我過去狐疑佛法的情況下,再度生起大信心,畢竟表相僧寶使我知道有佛法、恭敬佛法,但勝義僧寶卻能讓我打從心底相信佛法、理解佛法,進而有機會實證佛法,我認為這是勝義僧寶才有的可貴之處。